-
_NEWSDATE: 2024-06-29 | News by: 新京报书评周刊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在美国的亚裔移民。图为以亚裔移民生活和心理为背景的电视剧《怒呛人生》(Beef,2023)剧照。
新京报:获取世界性资本指向的是对“全球公民”身份的渴求。保罗·莫里斯等人曾区分过这之中的内部模糊性。它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基于世界主义的全球公民”和“基于倡导行动的全球公民”。你曾提到,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他们更多参与的是前者。如何理解这种参与?
马颖毅:这和我们既有的教育思维模式有很大关系。以中国这代留学生群体为例,他们在申请出国前其实会不同程度地接触一些培养“国际化思维”的课程,有的中国国际班还会组织学生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围绕艾滋病流行、全球女童教育等话题展开辩论。但仍然有学生跟我讲,说他们觉得这是“不完整的全球教育”。这些活动很难和具体个体的经历产生关联与共鸣。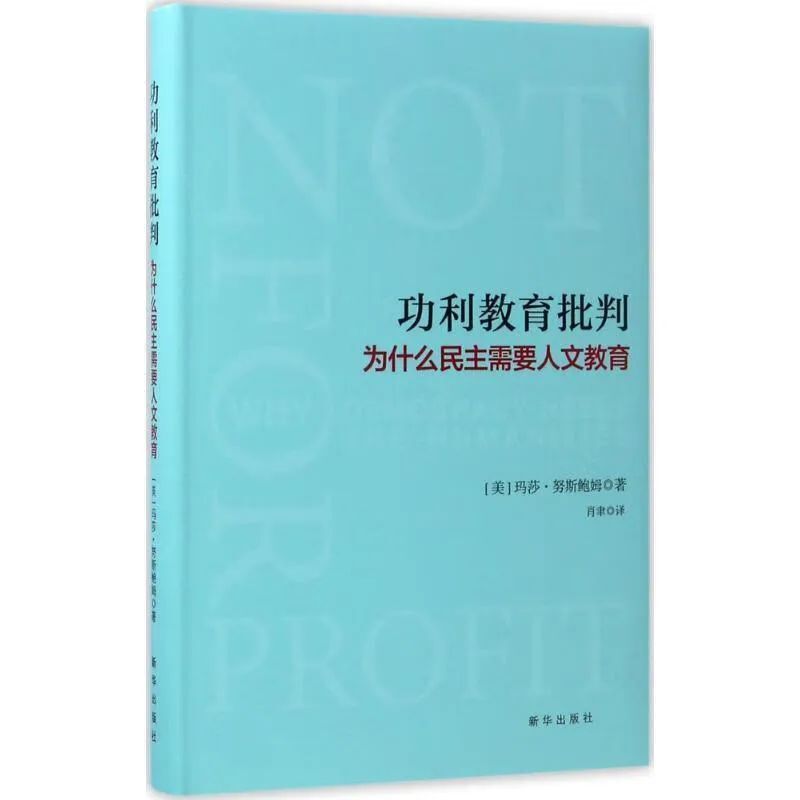
《功利教育批判:为什么需要人文教育》,[美]玛莎·努斯鲍姆着,肖聿译,新华出版社,2017年5月。
努斯鲍姆曾提出过全球公民身份基于的三种能力——批判审视自身背景的能力、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上其他人命运与共的能力、以及从他者视角看待世界的能力。这不仅需要认知上的打开,更重要的是通过真实地在多元群体中生活培养出的感受力。这点上中国学生常常在出国后才逐渐感觉到,大家参与世界主义的起点是完全不同的。
新京报:这也是我在读到书中关于“走向世界的雄心”这部分感触最深的。如果说90年代前后,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教育选择还意味着接触某种“现代而高级”的生活想象;那么,随着这些年现代化进程在全球的持续推进,它从一定程度上在缩小这种直观的差别。原先1.0的“世界性资本”在新一代留学生中逐渐转向2.0的“全球公民身份”。然而,新冠疫情以来这种全球性的流动速率大大减缓。这种向外的好奇在经历不同程度的收缩。据你观察,我们是否正在或将会面临某种“世界主义的回流”?
马颖毅:这种回流几乎是近年来一种全球性的趋势。而这又是一个相当广义而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国际关系,尤其是地缘政治,而个体在其中其实是相对无力的。我不认为这一代人不想去接触外部世界,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只能去面对。但无论如何,世界的大门已经敞开,这是不会逆转的。世界意识的种子已经种下了。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意识的作用仍然不可低估。我曾注意到,很多女生表示过留学后她们的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对她们的生活改变是很大的。回国之后,她们对职场中的女性不友好可能更加敏锐,从而影响她们实际的判断与选择。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世界主义的一部分。很多美国记者采访我时,他们有的认为,出国留学一定是受美国政治的影响。但实际不是,更多是生活态度层面、意识的觉醒和人格的教育,这些我认为比政治上的转变更加明显。-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