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NEWSDATE: 2025-06-09 | News by: 凤凰在人间 | 有0人参与评论 | _FONTSIZE: _FONT_SMALL _FONT_MEDIUM _FONT_LARGE
在“过来人”周子渊看来,青少年休学后,安全感是一个最普遍、也是应该被首先满足的需要,“尤其情绪状态比较严重或比较急性的阶段,当务之急是先让他缓下来,放松下来,一直紧绷着是好不了的”。
周子渊最后一次去小屋已经是两年多之前的事了,“它一直会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乌托邦,只是我不再那么急切地需要它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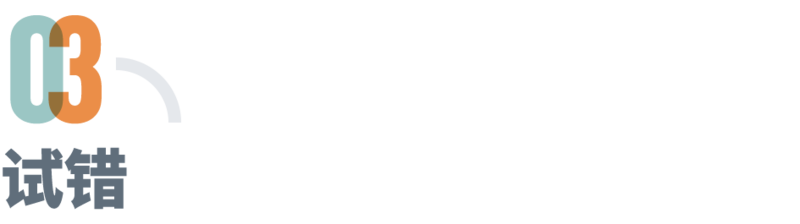
周子渊无疑是幸运的,一次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休学机构。更多家庭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错。
5月那个开放日当天,陈丽敏的儿子晓哲入住了这家休学机构。给孩子买好生活用品,离开北京前,陈丽敏最担心的是他的失眠。三四天后的夜里,她在河北的家中接到电话,晓哲哭着说自己睡不着,很痛苦,最初几晚有老师陪他,“后来人家让他走向独立”。陈丽敏听得着急,“他晚上需要人陪着,跟他聊天,要不他焦虑,一直胡思乱想”。
以博雅教育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也让晓哲觉得不适应。老师充满激情地讲苏格拉底、弗洛伊德,想引导孩子思考,但对于13岁的晓哲来说,这有些太深奥了。加上机构刚开始招生,晓哲之外只有零星一两个孩子加入,他找不到玩伴,大把的空闲时间里只能一个人玩手机。
深夜电话里儿子的哭腔让陈丽敏心里格外难受。一周后,她去北京接回了晓哲。
陈丽敏及时止损。还有一些孩子在休学机构待过数个月甚至一两年,但回头一看,只觉得“稀里糊涂”。
沈艺彤的15岁在北京一家休学社区度过。我问她在那里都做什么。“其实我也不太记得了,”她想了十几秒,反问自己,“我一整年都干啥了?”在她不多的记忆里,那里很自由:她有时醒得早,有时醒得晚,想参加活动就跟着参加,打羽毛球,玩桌游,上一些“不是很有学习的感觉”的课,都不想参与的话就到处晃悠晃悠。
◎ 沈艺彤休学后的艺术生活
她之所以待了一整年,只因为这是她妈妈的决定,“我只要在家就会刺痛她,我出去随便干点啥也比在家里待着强”。
同样是被妈妈的焦虑推动着,陈冉先后在上海两个休学社区各待过两个月。社区的周边环境不错,依山傍水,但她待过之后“反而更不舒服了”。
陈冉用一个词总结两个社区的共性:敷衍。宣传单上写得丰富:爬山、扫除、学画画、学外语......实际上,没有内部管理规则,没有日常活动计划,没有系统的教学体系。有时看着社区小院里被散养的鸡群,陈冉觉得自己和它们没什么区别,“感觉那儿像老年疗养中心而不是学校”。
更让她看不惯的是休学社区里老师和学生的相处模式,“感觉老师在故意讨好学生,为了让他们继续付钱留在那里”。比如,老师会刻意学一些时下的网络用语,和同学互称“宝宝”,夸人“萌萌嘟”,或是时不时冒出一句“要鼠了”——在陈冉看来,他们“一点老师的尊严都没有”。-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