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25-06-27 | ��Դ: �P�˾W�x�� | ��0�˅��c�uՓ | ���w: С �� ��
���S����齻ͨ�IJ��l�_������������ҕ�x�e���J���x�e���o�˵Ă�ʹ�H����������ڞ��̈́e������Ԋ���У��҂�����Ϥ�������S���Ǿ䡰������MҼ���ƣ�������P�o���ˡ���
��������½��x�����S�������̈́eԊ���������Ї������W�ČWԺ�IJ̵����ώ�������Լ������^ʧ��͒��������S���������Еr�������wՏ�c���⡣����ο���˵�Ԋ�䣬ͬ�rҲ�����f�Լ����м�į���О�Ó��
���S��������ȥĪ�͆�����녟o�M�r�����@�С��̈́e����Ԋ���҂���Ҋ��������녟o�M�r��֮�صĿ�����������ͬ�����A���������̈́eԊ�У��҂�Ҳ��Ҋ������u���@�����y�����g���Լ�Ҽ�c�c���ջ�����
���Ĺ��x�ԡ���Ԋ�e��ʰ�ˈ����С���С���}�龎�����M�����������ڙ����͡�
01.
�̈́e������p�ˣ�
������ᣬ߀վ��֪��
��Ҽ�괺�죬���e�Ű�֮�ᣬ���S�̈́eҼ�������㝓�����p�ˡ����㝓���e��ڣ�Ҫ���ؽ����ϼҡ�
�mȻ�����e���ϵĄ�ؓ�����Sÿ�겻֪��Ҫ�������٣��������㝓����߀��������Ҽ�ӵĐ��o֮�ġ����S��Ҽ������e��ā���ˣ������㝓���˺ܶ࣬����Ҽ�������������L��������Ҽ������Ҽ����w��֪����
���L�������ϣ�·;�b�h���������㝓���ǵĘ��ӣ����S����úð�ο������nj����ˡ������㝓���߀�l���@��Ԋ��
�}���o�[�ߣ�Ӣ�`�M��w��
����|ɽ�ͣ������ޱ��
�������T�h���������ǡ�
�����Ⱥ�ʳ������p���¡�
�þ��R�L����ͬ���c���`��
�Ю���������δ���G�顣
�h�䎧�пͣ��³Ǯ��䕟��
���\�m���ã����^֪��ϡ��
���S�������㝓���ţ��@��Ҽ���õĕr�������،��r����Թ�����f���@���}���ĕr�����]�ж���Ҽ߅���[ʿ����������������r�����O��Ӣ���`����t�š��@���r���Ƿe�O���ϵģ���Щ��|ɽ�[�Ͱ���ˣ�����ϲ�ޱ��
���S��ʲ�NҪ�@�N�f�أ��@��Ԓ�����ǰ������㝓��Ҳ�ǰ����������㝓��ٝ�P��ٝ�P�������ߝ����[��֮�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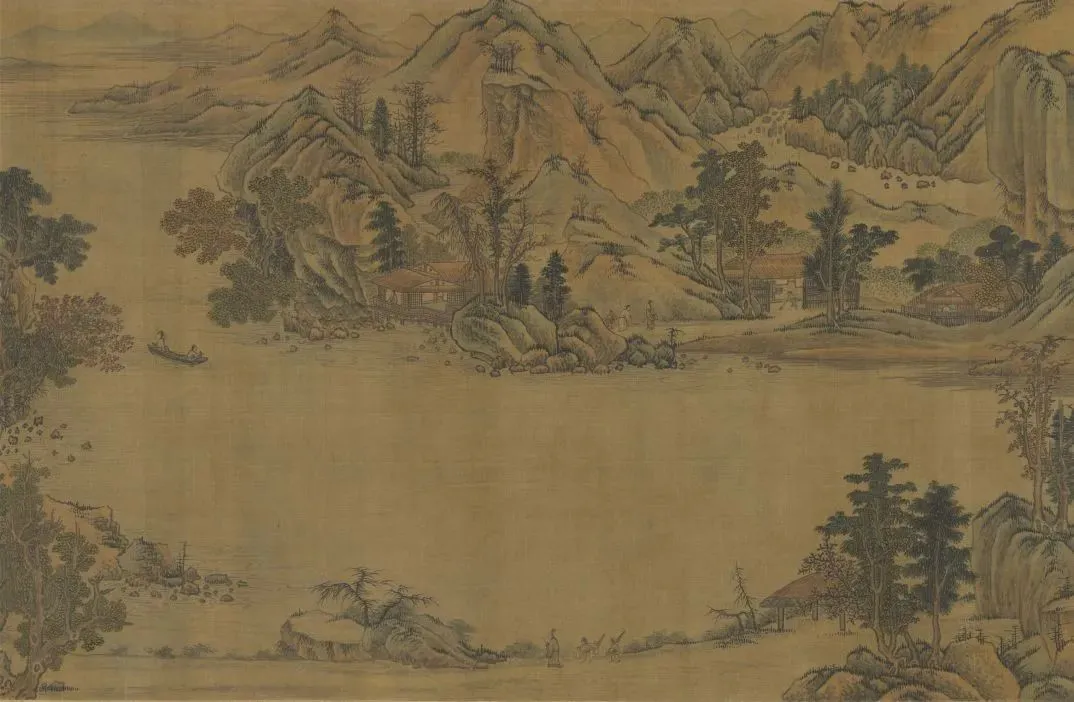
���S��ǧ���f�ֈD�����ֲ���
���㝓���ӿ��e�����빼ؓ�@����Õr����ϣ���������顣����ʧ��֮�ᣬ�y��������Լ����x�����Dz��Dz�ԓ���أ�
���S��Ԋ�������㝓�����˻ش𣺼�Ȼ�ѽ��h�����T���x�����@����ԇ�����l���f�@�ӵ��x�����e���أ��@���ڄ�ο���㝓��Ҫ���Լ����x�����ڡ���ڵ�ԭ��ֻ����顰���\�m���ã����^֪��ϡ�����]�����Ϻ��m�ĕr�C��Ӌ�\�]�еõ����ã��K�����f�@����֪��̫ϡ�١�
���㝓 �����@�ӵ�Ԓ�������Թ����Ҳ�������ʧ����Ĵ��������@�ӵĄ�ο������ǜ���غ�
���S�Ĝ���߀��춣������������㝓���ĵ��z�����y�^����ȥ���������㝓�����L���ѽ�Ҽ���ˣ����@���Ű�Ĵ����e����Щ�����Mʿ���ˣ��Ǵ��L����ġ������㝓���ܵ��ģ�ֻ�д������͡�
�r�g�^������֪���X�����Լ�Ҽ�o�ɣ����@�������e�h�hʎʎ��������S�����˃ɾ俴�Ƭ�м���f�P���������Ⱥ�ʳ������p���¡���
�@�ɾ�Ԋ���濴��ȥ��֪�����fʲ�N���䌍���S����ͨ�^�r�g����������㝓Ҽ��Ʒ�L��ڵĿ�ζ���֓��ڕr��������ǰ�Đ�㯡����S���Լ������㝓��ڵ��wՏ����Ҽ�N�dz�����ķ�ʽ�����f�o�����㝓��
ԭ����Ԋ�����@�e������ƺ��ѽ����_�ú܈A�M�ˡ����ǣ�Ԋ�˷·�߀��Щ���IJ��µĖ|����
��ǣ���߀��Ԋ�e���ˌ����㝓߀�l�г̵�����������Ҽ·�����������^�h���Ę��֣����^�³ǵ������������ܿ�͵����ˡ���ʲ�NҪ���@Щ�أ����SҪ�o���㝓���fҼ�N�Ą���@Ҽ·�ϣ�����Ҽ���˻�ȥ�ģ�������ᣬҼֱ��Ҽ�p�P������۾�����Ҽ·Ŀ���㰲ȫ���ҡ�
�@�����S��ף�����㝓Ҽ·ƽ�������Ҳ���ڰ�ο�����㲻�ǹεģ���Ҫ���żȻ�����\���۶�������������ᣬվ��֪����
���S���̈́e���㝓�ĕr��Ҽ��Ҳ�뵽���Լ���ɽ�����������s���Ěq�£��뵽���Ǖr�v�ķN�N���ס�
���S��L��Ԫ�꣨701�� ���������ݣ���ɽ��ʡ�����У�����_Ԫ���꣨721���Mʿ�еڡ��еڵ��@Ҽ�꣬���Sֻ�з�ʰ�q���ą��ӿ�ԇ�������Mʿ�����S�@Ҽ·�K�����ס�
��ʰ���q�����Ǒ�ԇ������r���Ĕ���Ư�������w��ˡ����ڮ��l�鮐�ͣ�ÿ��ѹ���˼�H�����@���^���У����SҲ�����^��С�x�ҵ�ʹ�࣬����܌�ʧ����ʧ�����ˣ������㝓������ͬ���ġ�
���\���ǣ����㝓����ٶȅ��ӿ��e��ԇ���K춵����Mʿ������Ҳ����ʢ��ɽˮ��@Ԋ�ɵĴ���Ԋ��֮Ҽ��
���㝓�������������������������Ƿ�����S���@����ο���P�أ����S���еġ����߀�l�@�ӵ����У����j�ʵģ����S�s�o����ȥ��Ҽ�N�d�d���^��������Ҽ�N�������ϽK��֪�����������@�N�����������������F��
02.
��������P�o���ˡ���
������У�Ҳ�̲�ס������n
����Ҽ�����죬Ҽ���m���h�еļ��������S�@Ҽ��Ҫȥ�̈́e�ģ���Ҽλ��Ԫ�������ѡ������������ֵ��е����С�
�@���̈́e�У��������ˡ���Ԫ��ʹ��������
μ�dz�������G��͑�������ɫ�¡�
������MҼ���ƣ�������P�o���ˡ�
����ʽ��e�����ӣ����S���ڴ����峿���L�e��������Ҽ�z������ζ����Ŷ��ԭ����μ���@�����Є������^���꣬������߅�����䣬�ѽ��_ʼ�L����ѿ������Ҽ�괺����ˣ����N������������Ҳ��Ҽ���µ��_ʼ�أ�
���S�cԪ��֮�g��������Ҽ�����С�Ԫ��Ҫȥ��������Ҽ���������I�ĵط���������Ҫ����Ҽ�ǰ;�h����I��
���S����Ԫ�������������еľƣ��ƺ��f��ҼЩ�{٩��Ԓ������Ͷ��Ҽ���ɣ���ȥ����������P���͛]���҂��@Щ������������ˡ�Ԫ��ҲЦ���Ѿƺ��ꡣ
���ǣ��̈́e�Ě����ĕ��@���p�Ɇ
�ڹŴ���Ԋ�͘���ҼЩ��r����P��Ԋ�����ᵽ�ġ�μ�ǡ��c��μ������֮�g����ҼЩ����P����μ�������ֽС���P���B�����������Ĕ��c�����dz�������
��������μ��������ӡ���M�����S�̈́eԪ�����@��Ԋ���҂��͕��l�X���g����Ҽ�N���n�����nԪ���@Ҽȥ���ª����飬��ǰ;�y�ϡ�
���Ƴ����кܶ�ʿ���x��ǰ��߅�����������ǣ��@���x�������y�ϣ��vȻ�܃e�һ���Ҳ������Ҽ�o�ɡ����ԣ��ڔ��c�e������P���B��������Ҽ�N��M�n����x�e��
Ԫ������ġ���S���y���D�������ֲ���
�Ŵ���ͨ���l�_���x�e�ĕr�g�����L���a�����L�UҲ�ܴ�֪��ʲ�N�r�����ط꣬����Ҳ�͛]�����طꡣҲ��ˣ�����������x�e���J���x�e���o�˵Ă�ʹ�H������������������[�f�ġ�������ǰΩ�Єe�����L���Mϧ�L�l����
�����L���Mϧ�L�l������Ҽ�N�M�˵��f�����ǡ������̈́e��֮�⡣���S���̈́eԪ����Ԋ���ᵽ�ġ���ɫ�¡������Ҳ���ڐ�㯡��UϢ�x�e��Ҽ��Ҽ���з��Ͱl���ɡ�
���S�֞�ʲ�N����Ԫ���f��������P�o���ˡ��أ�������S�˽�߅���ľ��r���������^�������v�ġ�
�_Ԫ��ʰ���꣨737�����£���������ʹ��ϣ�ݴ�����ެ���@Ҽ�����죬���S�ԱO����ʷ�����ݱ�Dz��߅��ο�ڌ�ʿ���@�����S��ƽ��Ҽ�γ�����ο߅���΄սY���ᣬ���S���ں������ι����й١�
�@�ӵ�߅�����v���o�����S��Ҽ�ӵ�����ɫ�ʣ���������ף�Ԫ������ãã��Į֮�ᣬҪƷζ����ȫ�µ�������ζ�����cԪ�����@�N���Ј����e��������Ҽζ���ډ��С�
��֪��ǰ�������\��δ֪�ġ��o���ģ�������̈́e��Ԋ�����ڲ����S�ຬ��δ¶�ĸ��顣
���SҲ�����;��Լ���������ζ����Ʒ�L��������ζ���S����������ǰ�M�ĵ�·�ϣ���Ҳ���Ά�Ӱֻ��̤����;����Ҽ�����������e�����L������Ԋ�е������Ǿ䡰Ҽ�����S�����¡���Դ������v�^�����б��g�x�ϡ�
��ʰ�q���^�ĕr�����S���������Mʿ���ã����\�ͽo����Ҽӛ����Ķ��⡣
���S�r��̫��ة���������Ę�������У����˲���˽�Ա������S�{�衣�@�����頿�浽���еĻ�λ���}���Pϵ���ʙ�����������Ƴ��ĵ�Y�����У���Ҽ�l��Ҏ���S�{��ֻ�ܞ�ʵ۱��ݡ��@�����ֱ��^���ĺ��������ͼӴ���ȾҼ�������o�˳�͢�����S�ɴ��ܵ����B�����H�����ݣ������ڽ�ɽ�|ʡ�ij�����ƽ�^���ȣ���
�����ʷ�]��ӛ�d�@���£�Ҳ���ˑ����@���^���������Hֆ���S��Ҽ����ڡ����S���˝���֮�ᣬ���w���εĹ�����������
�����f�ǝ���˾�}��܊������Ԋ�����ԿɸQҊ������r֮Ҽ�ߣ��������^�L�r�g���ڝ��ݣ�߀���^���ݡ���ꖡ����ݣ� �����ʡ����л��h�� �ȵء�
���ľ��w��Ҳ���Ǻ�����������Ҳ���������ڡ������ݡ�ҼԊ�����f�ġ��F߅�������ǘӣ�����̎��С���T�ˡ�
03.
�̈́eʧ�����ˣ�
Ҽͬ�c�^ȥ������]�ָ�e
�oՓ�������㝓߀����Ԫ�������S�����ڽ����Լ����Ё��wՏ���ˡ�
߀��Ҽ���̈́e�����S�ı����������Ͽ������Լ����@���̈́eҲ�����S������Ԋ�У��@��Ԋ�ͽС��̈́e����
���R��ƣ���������֮��
���Բ����⣬�w�P��ɽ�
��ȥĪ�͆�����녟o�M�r��
�@��Ҽ������ż���Ĉ�����Ԋ��ֻ�����䌦�ס�Ԋ�����Rٛ�ƣ��P�е�ԃ����������Ҫȥ���η����@�������f�Լ����������⣬Ҫ�w�[���K��ɽ��
�ڸF�_�c�����o���������q���e�����x���˷ŗ��c���[�������еđ�����ƽ���K�]������@�ӵķŗ���ƽϢ�����@Ȼ�ܵ������\�Ă��������Ը��VԊ�ˡ�Ī�͆����� ���g�ɰ�Ԓ�ľ��ǡ��㲻Ҫ���ˣ���IJ�Ҫ���ˡ��� �o��֮������Ա���
�@λʧ������ˣ� ϣ���Լ�����ĬĬ�x�_������녟o�M�r���� �t�����l����Ҽ�������L�ĚUϢ������ȥ־֮�ԣ��Լ��������������⡱�đ����c��ͣ�ȫ�����@��Ԋ���ˡ�
���S���@��Ԋ�Ĉ����У�ʼ�K���Ҽ����ǵ�λ�ã��ı����Ͽ�����ֻ�ǂ�ӛ��ߡ������H�ϣ������R��_ʼ���P�е�ԃ���ѽ�����������ǵ����ݡ�
���S�����˵ġ���֮��֮̎�O���P�ģ�������֪����w�[�ěQ���ᣬ߀���ن�������K�����˵ġ�Ī�͆�������ˡ�
���S��������@�N����£���ȉ��֡����ĝMǻ�����ͬ�飬�]���^�w���o̎�ɰl������Ҳ���m�������Ŀ�����
����녟o�M�r���@�UϢ�����H�����˪��l���ģ�����������ͬ�Ŀ��U���@�Nƽ���Ĕ�������Ԋ�ˌ�����������ͬ�顢��ο��Ҳ¶�������˽���������ף����
�w�[�K�������������xȥҲ�S�����ǽ�Ó���@���̈́e����Ԋ���c����Ҽ�𣬌������^ȥ����ē]�ָ�e������Ԋ�ĽYβ�����s���죬�б����o�M���z�����ͬ�rҲ�·���ҼĨͶ���h����������ζ���L��
���S���@��Ԋ�e���]���ἰ�̈́e����ʲ�N�ˡ����]�й̶���ָ���������f�����ˡ����S����Ԋ�����ߣ����Լ����������ȿ��Դ����̈́e�ߵĽǶȣ�Ҳ���Դ��뱻�̈́e��λ�á�
���S���������ƺ���������w�[֮��Ҽֱ����������С�
��ʷ֮�y��ǰ�����S�Y�����S���όә��F�����f�ƕ���ӛ�d���쌚ʰ���d��755�������S�����˽o���У�����Ʒ�ϣ����I�������죬�����H�����^�ߵ����ε�λ�����{���Լ��IJ��A���кܸߵ��ČW����
�����S���H��w�[��������ȥ�����T��ء�����ĕr�����@�N���Y�Լ�����Ҽ�����S�����£�������T��̎�N���������S�@�ӵ��ˣ����y�����Ҽ��Ҽ�³��e�y���ġ�
���Ă����£����S���_Ԫ���g����m�ڰl���ˡ���;���ۡ��H���x������ʷ֮�y�ĕr����׃�����������@Щ����įB�ӣ������S�����˂���̎��
�r�g���ɣ��D���g�ѽ��x�����S�{���������^ȥ�˺ܶ��ꡣ�_Ԫ��ʰҼ�굽�_Ԫ��ʰ���꣨733��734�������S���»ص����L�����@�r������ʰ���q�����@���܉���L�������٣���Ҫ����춏����g����Ρ�
���S�dz��JĽ�����g�@λӲ�����ࡣ�_Ԫ��ʰ���� ��735���������g��ʼ�d�h�������S����ʰ�z�������ġ��Iʼ�d�������ͱ��_�ˌ������g���Jͬ��
Ԋ���f�Լ����ԡ���ʳ���⡱�����ְ��^����֮������Ҫ��������ϣ���܉�����Ч�������˰��g�����u�����������n���\������������Ո���gҼ��Ҫ�Ĺ����ē��˘����l����Ҫ��˽�˽������������
�������S�ЙC�����S�����g�@�ӵ�Ҽ��������Ҽ���I�ĕr�����g�ڳ�͢�б��ŔD�ˣ�Ҽ�H���H�������ָ����ŔD�£��_Ԫ��ʰ���꣨736��ʰҼ�£������g�T֪���¡��_Ԫ��ʰ���꣨737�����£������g�ֱ��H���G�ݴ����Lʷ��
Ҽ����f����ʷ֮�y���Ƴ�ʢ˥�ķ�ˮ�X�����H�ϣ�ʢ˥���D׃���C�����_Ԫʢ���r�����gҊ�š����ָ��Äݕr�ͷ����ˡ�
�����g���𣬲��H����������������ĽY����ͬ�rҲ��־��������������ĩ�r���\���Ƅ������a�����_�����εĽY����
���ǂ��r���������F������΄���׃��Խ��Խ��������׃��Խ��Խ�ڰ�����ֱ��ʿ�ܵ�����������ٳ�Ҋ���^���¡�
���S����������څ�������g������߀�ܵ������g�����غ���Ρ���ˣ��������g���������ܵ��ŔD�ᣬ���S������Ҳ�����^��
���S�������F���������Ο��飬����������ȥ���������е��ӱܬF�������O˼��������B�ȵõ����MҼ���lչ��������˳�������̨���w�[��ɽ����ȥ��
������ڡ��ꏈ�ٸ����@��Ԋ�Ќ��µğo��֮�P����o�L�ߣ���֪���f�֡������S���Կ����@���r�ڵ���֮�ľw�����ע�⡣
04.
�̈́e�������ˣ�
���f�����Լ���
�ٴλص����̈́e���@��Ԋ�e���҆������S�̈́e�ăH�H�����ˆ�����ǣ������������f���Լ������̈́e���㝓�r�Ĝ���غ��̈́eԪ���r�đnϲ���룬�ٵ��@���̈́e�r�����O�������@�����̈́eԊ���ʬF�˲�ͬ�����S��
�҂������ƺ����Կ��������S����u���@�����y�����g�����Լ�Ҽ�c�c���ջ������ջص���ȫ����Լ����ǷN��B��
�@�r�����mȻ�кܶ�IJ��������߀��ͦ���^ȥ�����Sֻ���f�Լ���Ҫȥ�ǰ�녟o�M�Ěw�[֮̎��߀�]�е���������T��̎�N���ĵز���
Ȼ�������S�ڰ�ʷ֮�y�е����轛�v�����ǷN���[���c����֮�g�u�[�����飬����Ҽ�N�ݳ����^����ʷ֮�y�����Ğ��y�Dz���ĥ��ģ��������c�@���ش�Ěvʷ�¼������r�����ɱ���ؕ��ܵ����������SҲ�����⡣
��ʷ֮�y���l�r���������������������S�]�и��ϴ�����R���������L�������\���ܫ@������ɽ�ˌ����S�PѺ����ꖣ����������¡����˲����\�����ã����S����ҼЩˎ�������Լ�������������
�@Ҽ�꣬���S�ѽ���ʰ��q�ˡ������@�ӵIJ���������������Σ�U�ġ���ÿ������������������ʹ�࣬���@Щʹ�࣬���Ȳ��������e��ʹ�ࡣ
���r���l����Ҽ����� �����顣���\����������̳ش���ĕr���ȱ�������̔����@����Ҽ�����˱��ݸ��裬�cף�����Ą����������Ђ������Ę����������ࡣ���F���P�P���x���~���ؾܽ^�˱���Ҫ�K����������ȥ�������\����������춑��R�����ѳ����
���S �f���@�������ᣬ�dz��y�^��͵͵������Ҽ��Ԋ��
�f�������Ұ�����ٹٺ����ٳ��죿
�ﻱ�~��Ռm�e�����̳��^����ҡ�
���@��Ԋ�У����S˼��ʇ���˼�������ڣ��f��o����춹P�ˡ�
��������SҲ����@��Ԋ�ի@��ҼЩ���\���@��Ԋ�;ܽ^���\���О飬ʹ���S�õ������C�ڵ�Տ�⡣���C�������������܂ι�λ�IJ����ѣ��]�Б���������ͽ���������ܵ����N�����飬���S�K춻��U���ġ�
���ǣ��@����Ҳ�����S�F�������е�Ҽ����׃�ʣ�����Ҽ���Ľ��v�����ă��Įa�����қ_�������SҼ�����ף���ʹ��͢��������Լ����������Ҳ�ѽ��������ˡ�
ǬԪԪ�굽��Ԫ���꣨758��761�����@�����У����S�Ĺ��Խ��Խ������Ҽ�������S�K���J���Լ��dzɹ��ġ�
��ĺ��КU�r�����ţ����A��ȥ�����������ĺ�X������װl׃���ء������U��Ҽ�����S�����¡���
�@��Ȼ�������ڬF���������������ķN�N���ģ��T����ѡ���ĸ�����ȡ��e�x��֮ʹ���H�ٱ���֮ʹ����ʷ֮�y�����Ľ�֮ʹ�����ڂι١�ʹ������ױ�����֮ʹ���������m�W���`��������e�y�����N����֮ʹ��
��ȥ��ǰ��Ҽ�꣬���S�D���Е���ة���@����Ҽ�����ι�����ߵĹ��A��Ҳ����������֮����Ԫ���꣨761�����죬���S�ǷN��Ҫȥ������녟o�M�r��֮�ص����飬��Ȼ�]�и�׃��
���o�ʵی��ˡ�؟���]�ܱ�����Ո����ȥ�Լ�ȫ�������Św��@��Ҳϣ���Դ˓Q���ܵ����N�ط�������
����ڰ�ʷ֮�y�н��v������׃�ʣ����S�������Լ���Ԋ�e�����ᵽ���@�ƺ��������S�����в������_��Ҽ�����̡�����ʹ���]����ɢ��ֻ�DZ������������ڲ������gҲ��������¶���c�̈́e���˕r��Щ�ğoϢ�ĵ�������Ҽ�ӡ�
��������S����ס�ھ������y���e�������V�ŷ��£��������ᣬ���㪚�����ԶU�b���¡��ǘӵ����L�r�⣬Ҽ���������̈́e��λ��֪��������Ҽ�ӣ�Ҳ�ǡ���녟o�M�r���ɡ�- ����Դ�����ý�w�����ݲ�������վ������
- ԭ��朽�
Ŀǰ߀�]���˰l���uՓ, ��Ҷ����ڴ����ĸ�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