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5-07-25 | 来源: MSNBC/钛媒体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特朗普 | 字体: 小 中 大
图源:央视新闻
郭霆:是的。实际上我感觉,过去几年好像美国在各方面都在学习中国这套系统。中国医保谈判运行几年后,新药上市,药企可以有选择,比如可以去谈也可以不去谈。如果谈进了,就有医保支付,患者负担小很多,同时量可能增长很多。
美国从2003年开始,法律规定政府不能跟药企谈判价格,但这事在2023年被打破了。拜登政府的IRA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引入了一个药品谈判机制,要求美国医保局每年选择10-20种药品谈判,但它不是选择新药,而是在市场上卖了9-13年的药,逻辑是“你一个药卖了这么久,钱是不是赚够了?没道理继续永远收这么高的价格”。整个医保谈判的思路和操作,和中国及其他做药价谈判的欧洲国家比较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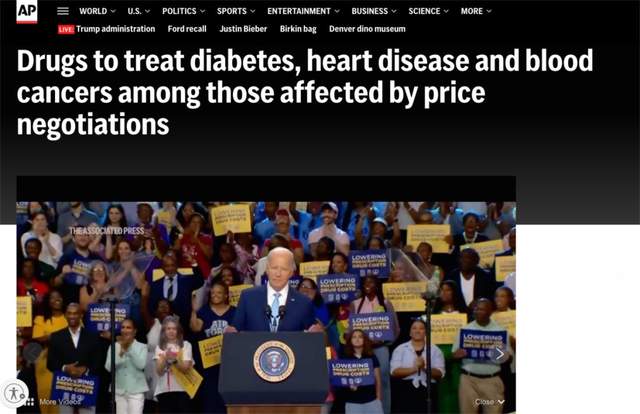
图源:美联社
泓君: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药企研发一款药物,平均成本可能达10亿美元。要让药企持续有动力收回这些成本,一开始大众确实需要支付较高的药价,以此维护药企的创新动力。然而,当药品已经销售多年,药企获得暴利时,降低药价对大众而言更为有利,这实际上是一种平衡与博弈。
郭霆:道理上确实如此,但实际背后的数字极为复杂。从纯经济学角度讲,风险越高,就需要越高的回报。研发新药风险巨大,投资一些公司可能就打水漂了,但也有公司研发成功,所以需要高回报来补偿这种风险。据经济学家对过去几十年的统计研究,医药行业平均回报率并不是非常高——这里计算的不是股价回报,而是药企自身的投资回报率,算出药企的投资回报率仅比20%多一点。这表明经过多年各方博弈,医药行业回报处于相对合理的水平,它并不是一个暴利行业。当然,单个成功的药品品种,经过十年研发及七八年上市销售,把市场打开,把患者、医生教育之后,单年利润率确实很高。但从全行业、全周期来看,回报率仍相对合理。
所以,从行业角度,药企觉得仅让小分子药销售9年、大分子药销售13年,就直接进行价格谈判,而且谈判降价幅度很大,就不太合理。从净现值(NPV)角度计算回报,药品最赚钱的就是最后几年。
泓君:因为市场做开了,量开始走高了。
郭霆:对,因为药企整个收入曲线是爬坡的。一旦最后几年价格被砍,整个投资回报曲线就变了,这会对投资决策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
其中,法律规定小分子药上市9年后就可以入选谈判,大分子药需13年,药企认为这一点很不合理,行业协会也在争取向国会取消这一规定。这也是特朗普行政命令及后续跟进的卫生部细则中提及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泓君:他们倾向于让小分子药也按13年期限吗?
郭霆:你问了一个关键问题。药企肯定希望两边都变成13年。但看政府发出的文,只说要把两边变得一样,具体最后是都变13年还是9年也不知道。我个人相信,大概率会两个都变成13年,或接近13年。
泓君:其实这对药企是利好的,拜登看来在政策上又给了它们一些宽松的空间。
郭霆:医药行业它有很多复杂的逻辑,而且研发决策远在药品获批上市前很多年就做了。现在一个政策会影响到许多临床开发计划。比如癌症药,一个小分子药在开发时一般怎么做?
比如,一个患者刚诊断出肺癌,CT一扫肺部阴影,做个活检,是IIIB期或者IV期转移性肺癌,这是一线癌症。如果患者已经历好几线治疗,用了化疗药,就已经是生命垂危的末线患者。肺癌一线治疗或末线治疗,在药物监管里算不同适应症,药企在做临床的时候它是都得做的。在计划不同临床时,以前肯定先捡容易的做,先从后线做起或先做小的,先把药品弄上市,再慢慢做大。-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