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5-08-05 | 來源: 新京報書評周刊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那麼,公眾人物公開自己的精神患病經歷與公眾認知有何種關系?人們在期待何種精神類疾病敘事?當抑郁症再次因為娛樂話題成為焦點時,本篇文章將討論被納入公共討論的精神類疾病是如何在大眾文化圈層完成“破圈”的,以及影視劇等媒介從何種角度參與了這些敘事。
撰文|帕孜麗婭
被想象的精神疾病
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作為健康反面的疾病始終與我們相隨,正如蘇珊·桑塔格所言,“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壹屬於健康王國,另壹則屬於疾病王國。”人類對疾病的認知也壹直在變化,這壹點在精神類疾病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不同於常見的生理類疾病,精神類疾病常常難以看到明顯的病灶,這種“不可見性”又使得精神類疾病具有“難理解性”。這些疾病常常以某種感覺的形式出現,但感覺又是很難共通的存在,就像男性很難真正理解女性的痛經壹樣,健康的人也很難想象雙相情感障礙患者兩極化的情緒。精神類疾病患者可以用壹些形象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感受,但這些表述也只是給聽眾壹個想象空間,不斷想象患者所經歷的壹切。想象固然有助於我們理解,但難以涵蓋所有情況的想象有時反而會限制我們的感受,進而影響我們對這些疾病的認知。
盡管現代社會已經不會將精神類疾病視為“中邪”,更不會用“巫術”或其他儀式進行驅趕,但大部分人對這些疾病的了解依然停留在他人講述和媒介呈現中。比如,認為抑郁症是壹種活力喪失,表現為情緒低落、失眠、食欲減少、不願出門;而雙相情感障礙則是又有抑郁期又有躁狂期、在兩種極端裡反復掙扎的疾病;至於進食障礙,那就表現為暴食或厭食、消瘦、過度減肥;焦慮症則是心慌、坐立難安甚至驚恐發作的代名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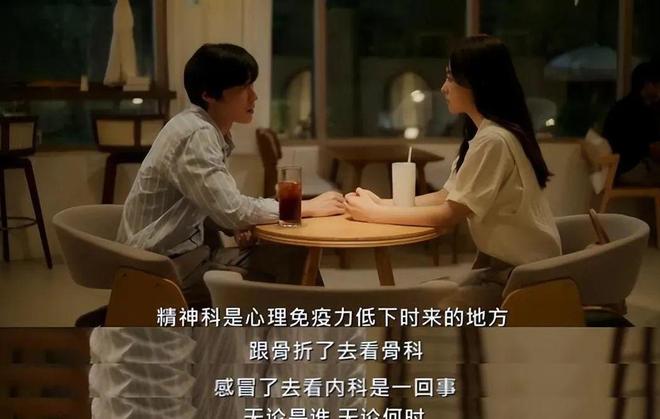
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劇照。
影視劇、綜藝甚至是社交平台,共同形塑了我們對這些疾病的基本認知,但與此同時也使得我們將精神類疾病標簽化,對各個疾病形成了壹些固定認知。於是,當有人表示自己患有某種精神疾病時,習慣性地代入這些固定認知,來反復觀察當事人與標簽是否壹致。與標簽壹致時,我們可能會表示同情,與標簽不同時,則忍不住懷疑疾病的真實性,怎麼可能笑得這麼開心,她是不是裝病?
這或許是精神類疾病的特殊之處。我們不會要求壹個骨折病人拆開石膏或者拿出X光片子看看傷口是否符合我們對骨折的認知和想象,但精神類疾病的無法外顯使得患者時常陷入壹種自證,或者證明自己真的生病了,或者證明自己雖然生病了但依然有學習和工作的能力。這種生理性疾病不需要經歷的困境,對諸多精神疾病患者來說可能是最常見的體驗。
羅伊·理查德·格林克曾指出,文化創造了“正常”,於是有壹部分人被歸為“不正常”,而精神疾病患者正是壹群因為不符合“正常”標准而遭受種種污名化的“不正常”人群。顯然,在這樣的語境中,“正常”是被建構的,我們建構了“正常”,使得另壹部分人“不正常”,但現實中,這些“不正常”的群體可能既不符合“正常”的標准,又無法完全符合被建構的“不正常”標准,為了能夠被歸類,他們只能反復拿出自己“不正常”的證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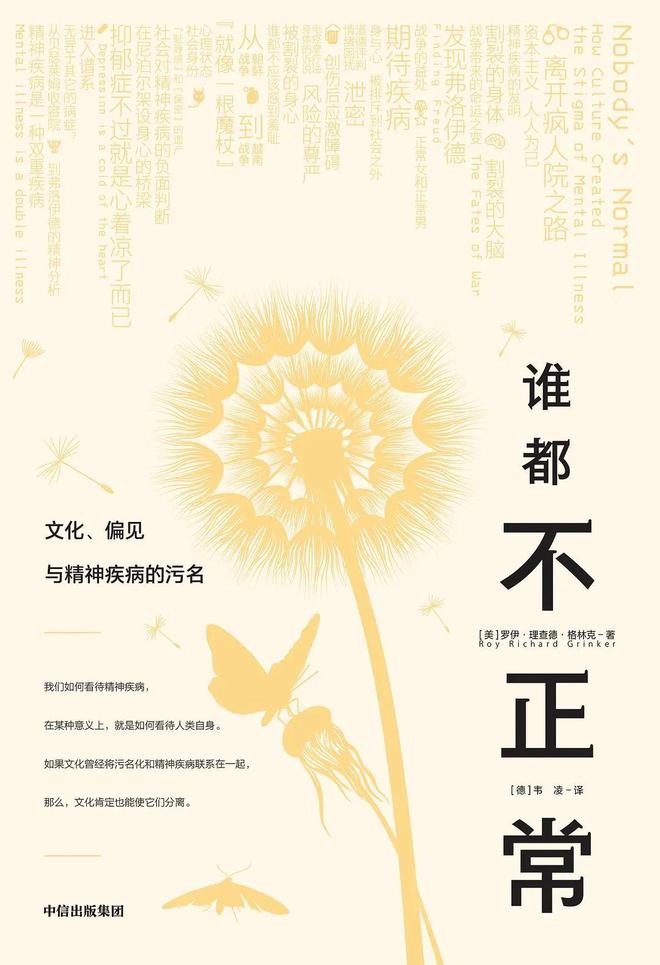
-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