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4-11-17 | 来源: 京京博客 | 有0人参与评论 | 字体: 小 中 大
对于很多华人来讲,米兰·昆德拉是一个老朋友,从他作品的标题来看,总是带着“庆祝无意义”之感,带着悖论和狡黠意味。这位以《玩笑》闻名于世的作家,一开始就把人的荒诞处境看得透彻: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能给我们开残酷的玩笑,只因为我们被一种前所未知的非理性所控制,因为我们不能敏锐地提出问题。《慢》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部书评,一部米兰·昆德拉的奇特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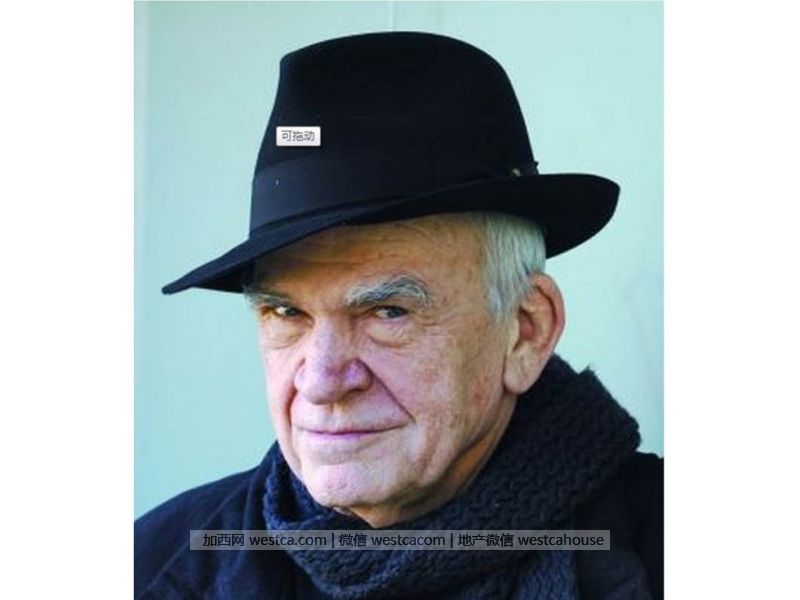
米兰昆德拉(图片来源:南都网)
可以说,昆德拉提供给读者的,是智性的愉悦与幽默,而哈维尔要求的是灵魂的自足,道德的重负。故而,昆德拉的嘴角总有抹不去的讥笑,对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面,是刻薄的,带着调侃与挑衅,他甚至对压抑型体制中那反抗的政治激情,也表示质疑,视其为政治媚俗。
1995年,米兰·昆德拉发表了第一部法语小说《慢》。之前二十年,他离开了故乡捷克。之前十四年,他入籍法国。《慢》是他脱捷入法的最后一道手续,是他自我颁发的法国文学人身份证。昆德拉的小说里永远有一个叙事者,对第三人称的其他人物、对别人的故事时而沉思时而嘲弄。这一次,这个叙事者“我”是位道地的法国人,浑然不知捷克事。他上接法国旧小说的文脉,以法国人的立场思考当下人生。我不懂法语,不知道法国评论家有没有议论过昆德拉的这一番做作。书里也有一位捷克人,昆虫学家,不幸、可笑、屈辱、猥琐,很像帝政时代误入巴黎的外省乡下人,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处处遭遇冷眼。
从某种意义上讲,《慢》不是一部一般的小说,它更像是一部书评,一部小说体的书评。书评未必要“评”,更高级的书评,是和原作的对话,是以原作作者为假想读者的交谈。
让昆德拉激动的小说是《明日不再来》,初版于1777年,作者维旺·德农。从《慢》的第二节起,《明日不再来》被反复介绍、引述、改写。小说结尾处,昆德拉笔下的人物和德农笔下的人物相遇,“我”在远处观望。《明日不再来》是《慢》的写作动机,它激发了昆德拉的无穷想象。德农讲完他的故事,昆德拉说,这是一个好故事,我来告诉你,两百年后,你的故事应该怎样读。
《明日不再来》是一个骑士偷情的故事:贵妇人T勾引了一位二十岁的年轻骑士。他们一起来到T夫人的城堡。与夫人的丈夫共进晚餐后,骑士和T夫人开始了他们的夜晚。像一幅三联画,先是花园散步,然后小屋做爱,最后密室尽欢。第二天早晨,骑士发现他是被用来掩护T夫人真正情夫的挡箭牌,经此良宵后,明日不再来。虽然他知道这是一场骗局,还是满怀感激、快乐地离开城堡。昆德拉说,这个故事“最像代表十八世纪艺术与精神的文学作品”。
两百年后,《慢》的故事展开:城堡已经被改建成豪华酒店。一个国际会议在这里举行,各色人等蜂拥而至。那一夜,也有偷情,也有骗局,更有形形色色的欲望表演。但一切都变调了,德农故事里朦胧夜色下的浪漫艳情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嘈杂、狂暴、歇斯底里、丑态百出……连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在这里也会变得“叫人讨厌”。
昆德拉非常明确地让《慢》和《明日不再来》形成对比:城堡与酒店;私人聚餐与公共宴会;马车缓行与机车狂飙;骑士与知识分子媒体人物;避人耳目与唯恐天下不知; 密室中轻怜蜜爱与公众前声嘶力竭……最重要的对比:慢与快。最后结果:幸福与失落。用小说体书评的视角梳理《慢》的脉络,你一点也不会觉得拥挤、散漫、混乱。《慢》体现了昆德拉对现代性的思考和控诉。他有关速度和缓慢的论述,极其精彩,可以说是对当代生活最智慧的哲学思索之一。
昆德拉喜欢自由的慢生活。在那样的生活里,甚至连T夫人的偷情阴谋都恩泽四方皆大欢喜回味不尽。那种偷情,过程悠长、细节饱满,心机并不血腥,是值得记忆,最终果然被甜蜜追忆的生活。那时候的色情,可以上升为艺术、上升为文学。而现代的高速度、快节奏,令色情只剩下肉欲和权力争逐,只剩下征服或者被征服的结果。
《慢》里面的情爱,并没有多少阴谋算计的背景,却毫无美感。现代人再极端都不美学。昆德拉甚至让书中人物无所顾忌地聊到菊点。不过这个菊点可能是人类情色文字里最无精打采、心事重重的眼。用昆德拉形而上的脑浆浸泡,再被批评家的哈欠风干,它很可能永远地陈列在昆德拉的小说博物馆里,成为一只阴郁地打量人类的哲学之眼。
这就是天才的书评。一部书让读者领会两部书的妙处,还能想到很多事。
米兰·昆德拉生平简介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尔诺。父亲是钢琴家、音乐教授,当过音乐学院院长。
昆德拉孩提时代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度过的。在这里,他经常悄悄地听父亲给学生讲课;父亲亲自教他弹钢琴,引领他一步步走进音乐世界;任意浏览父亲众多的藏书。十来岁时,他就已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捷克的和外国的都有。十三四岁时,正值二战时期,他师从捷克最出色的作曲家之一保尔·哈斯学习作曲。后来,哈斯先生被关进集中营,再也没有出来。昆德拉始终把他当做“我个人神殿中的一位”。他写下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保尔·哈斯》。1947年,18岁的米兰·昆德拉成了捷克共产党的一员。
1948年,19岁的米兰·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后,经常去听音乐课。后来又到布拉格电影学院读电影专业,并在那里毕了业。迷恋音乐的同时,昆德拉还投入到了写诗的热情之中。从昆德拉的第一本诗《人:一座广阔的花园》中,人们就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当时的捷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的诗歌到处泛滥。而昆德拉的诗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
1956年,他完成了在布拉格电影学院的学业,留校当了一名教师,教授世界文学。留校后不久,昆德拉开始大量阅读理论书籍,并继续大学期间就已开始写作的《小说的艺术》一书。从25岁开始,至27岁完成,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写作此书的直接动机是获得教师资格,也有教学方面的需要,同时还为了解决文学实践中的一些困惑。《小说的艺术》1960年出版,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昆德拉的笔触几乎立即伸向了戏剧。他在自己的祖国先后写过3个剧本。1958年是个具有实质意义的年头。在写剧本的间隙,花了一两天时间,他就写出了《我,悲哀的上帝》。这是他生平写出的第一篇小说。写完第一篇后,他又陆陆续续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一共写了10篇。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时间跨度整整10年。这些短篇小说以《可笑的爱》这一总标题分3册出版。而真正开始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作品是小说《玩笑》,该书连出3版,印数达到几十万册。《玩笑》还被拍成了电影。
1968年8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玩笑》被列为禁书,立即从书店和图书馆消失了。在东欧国家,除去波兰和南斯拉夫,它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昆德拉党籍被开除,在电影学院的教职也被解除,所有作品都一下子从书店和公共图书馆消失,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1975年,在法国议会主席埃德加·伏奥雷的亲自请求下,捷克政府特准米兰·昆德拉和他的妻子前往法国。昆德拉到法国后,经由法国作家费尔南德斯的举荐,先在雷恩大学担任助教。流亡之初的一段时间,昆德拉成了地地道道的公众人物。他上电视,接受采访,发表谈话,撰写文章,利用各种场合向人们讲述苏联人侵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1978年,他们定居巴黎,并于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1984年,昆德拉发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浦·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
1989年,昆德拉老家布尔诺的阿特兰蒂斯出版社主动与他联系,表示愿意出版他二十多年来在祖国一直被禁的作品。昆德拉欣然同意,但明确规定只能出版那些他本人选定并审阅过的“成熟之作”。
1995年秋天,捷克政府决定将国家最高奖项之一的功勋奖授予米兰·昆德拉。他欣然接受,并以书面形式回答了捷克《人民报》记者的提问。谈到获奖感受时,昆德拉说:“我很感动,也许可以说,尤为让我感动的是瓦茨拉夫·哈维尔给我的信。特别是信中的这样一句话: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