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18-10-31 | 来源: 土逗公社 | 有0人参与评论 | 专栏: 金庸 | 字体: 小 中 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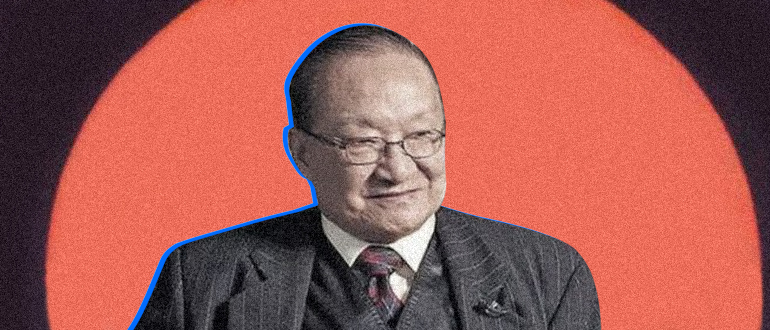
摘要:金庸的故事是中国史,金庸的传播是改开史,金庸的情感可说是救亡史。他唯独与革命史无关。
——网友
10月30日下午,中国武侠小说泰斗、香港《明报》创办人查良镛于香港逝世,享年94岁。
自1950年代开始,查良镛便以金庸为笔名创作武侠小说。我们耳熟能详的《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均为其代表作。
作为华语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可谓影响了几代华人读者。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会cos靖哥哥和蓉儿,给贪吃邋遢的小伙伴起“洪七公”的外号,打闹时使出“九阴白骨爪”、“降龙十八掌”等招数。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政客则会直接在议会互斥对方是“岳不群”、“左冷禅”。无论是绞尽脑汁将小说原着带回学校在课堂上偷读,还是定时守在电视机前紧张地等待剧情进展,金庸的作品永远成为了我们不可替代的记忆。
如今,斯人已逝。当长大后的我们取下回忆滤镜,重读金大侠的作品,这才发现:金大侠的创作史,忠实地记录了时代思潮的变迁。
从《射雕》到《神雕》,从集体到个人
对于《射雕》,倪匡先生有两句评价颇耐人寻味:
金庸写人物,成功始自《射雕》,而在《射雕》之后,更趋成熟。
《射雕》在金庸的作品中,是比较“浅”的一部作品,流传最广,最易为读者接受,也在于这一点。
这两句话说得很中肯。相比较晚期的《连城诀》、《笑傲江湖》、《鹿鼎记》等作品,大抵那时金庸还不会那样赤裸裸地刻画人性的阴暗面。《射雕英雄传》的人物故事总是那么善恶分明、正邪对立。
失去了“人性”这一1980年代以来“新时期”文学界的政治正确,《射雕》自然失之于“浅”。然而,倪匡先生很敏锐地看到,此书是金庸的转折之作:
《射雕》中,金庸还在强调群众力量,强调集体,尽在个人力量之上,这种观念,集中在君山之会,郭靖、黄蓉被丐帮逼得面临失败这一情节上。但是这种观念在一再强调中,实际上已出现了崩溃的迹兆,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个体的力量在前头,金庸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接着又写了郭、黄二人,打败了丐帮的大批人。英雄人物,毕竟是个体的、独立的。和群众的盲目、冲动,大不相同。
这种群体观念崩溃的迹兆,始于《射雕》,而到了《神雕侠侣》,杨过在百万军中,击毙蒙古皇帝,已彻底转变完成。自此之后,金庸的小说中,始终是个体观念为主了。
原来,《射雕》到《神雕》的转折,便是从集体到个人的过渡。
红花会壮举是一场class斗争
按照倪匡的逻辑,金大侠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无疑是一部够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小说。金庸本人也曾跟池田大作坦白:“我学《水浒》写《书剑恩仇录》。”我们不会怀疑,红花会确实蛮像聚义厅的。徐天宏巧骗玉瓶像是吴用智取生辰纲;骆冰偷新娘衣活脱脱鼓上蚤盗甲……故事情节倒在其次,关键是《水浒传》之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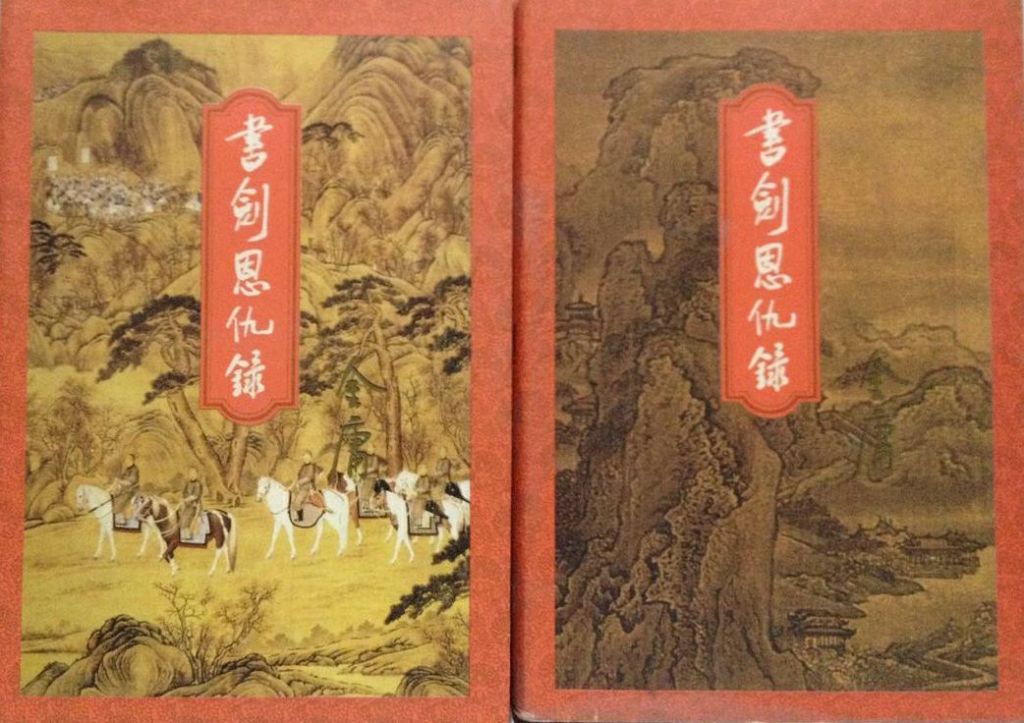
- 新闻来源于其它媒体,内容不代表本站立场!
-
原文链接
原文链接:
目前还没有人发表评论,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