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2024-02-15 | 來源: 精英說 | 有0人參與評論 | 字體: 小 中 大
在雲南大理的街頭,擺上壹個方寸大小的攤,放上幾本原創的詩集,喝茶賞雲、小狗守攤,這個擁有白皙皮膚、長相秀麗的 00 後女孩,因為“壹人壹狗浪跡天涯”的生活方式被人稱為“流浪詩人”。

女孩慵懶地坐在地上,文藝范拾足,有人聯想到著名女作家叁毛,猜想她是精英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兒,在這詩情畫意的地方采風、體驗生活;也有人認定她是在作秀,衣著暗淡、攤無定所,只是想靠劇本吸引流量......
伴隨著女孩的爭議越來越多,討論聲終於吸引了UP主@到處走的壹林做了壹期深入采訪:
當人們真正開始了解她“躺平”背後的故事,了解她愚昧無知的原生家庭和沾滿血與淚的童年,不免感到心酸和唏噓;而她為了接受教育,14 歲時與父母決裂、多番以命相博的勇敢,更令無數網友為之動容。

“家人永遠都是在想著,
怎麼樣把你嫁出去”
這位 00 後女孩名叫康韶華,今年21歲,來自甘肅臨夏。亂山多破碎,險峻徑逼仄,是這片土地先天不足的自然稟賦。因為地處祖國西部邊疆幾大地理單元的過渡地帶,所以這片土地上自古民族眾多、信仰(电视剧)復雜。康韶華就出生在壹個虔信伊斯蘭教的東鄉族家庭,虔誠的信念,卻讓整個家庭充滿了束縛和壓抑......
眾所周知,《古蘭經》雖然在社會層面承認男女價值平等,但在家庭層面卻認定只有男性才是壹家之主,所以穆斯林對女性壹直以來的規訓就是,“出嫁前,好好幹活,聽爸爸的話;出嫁後,做好本分,聽丈夫的話。”
而比起其他民族的穆斯林,東鄉族的男女有著更涇渭分明的物理空間歸屬,即“男主外,女主內”。其中,女性的“內”幾乎僅限於自己家的院落以內,不能隨便上街,不能到處亂走,甚至不能去上學。
“女孩早晚要嫁人的,讀了書也沒用”,這種腐朽的觀念根深蒂固。壹家之主們甚至擔心學校男女混雜會影響女孩和家族的名聲,通常早早讓其輟學回家,學習如何成為別人家完美的妻子:洗衣、做飯、喂牲口,永遠不能停下來。
直到15、6歲,作為壯大本家族、本教派實力的工具,女孩被說了媒,訂了親,成了婚,變成女人,便從屬於夫家,就連外出、回娘家等等再正常不過的活動,都必須需要征得丈夫和公婆的同意。
縱觀東鄉女性的壹生,唯壹自由的時間,只有等到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但很多飽受摧殘的老人,自己重獲自由後,或許是心理扭曲,或許是完全被規則馴化,她們非但不庇佑孫女,反而成了毒害孫女的劊子手。
康韶華14歲那年的某天,因發高燒身體不舒服,沒能完成家務,躺在床上休息的她沒能等來家人的噓寒問暖,反而招來了奶奶的指責和謾罵。她唆使自己的兒子責打自己的孫女,說辭是:你女兒都這樣了,你現在不打她,以後到了婆家,她公公打她,她老公打她,她該怎麼辦?
父親在短暫的猶豫後,真的找來壹根碗口粗的棍子,對女兒瘋也似的毒打,打到手指斷裂,打到動撣不得,攤臥在床。
如此殘暴,康紹華的母親,那位16歲就嫁進這個家,當牛做馬至今還沒熬成婆的母親,難道對自己的女兒就沒有壹絲絲憐憫嗎?
有的,但她更怕女兒行差踏錯壹步,將來嫁不出去,讓家族蒙羞,為家庭增加負擔,於是看緊了大門,防止她逃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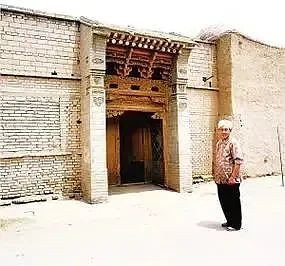
在苦澀的歲月裡,書籍是康韶華唯壹的救贖。她從小喜愛讀書,尤其是文字和詩歌令她著迷。即便是 5 年級時就被奶奶要求強制輟學回家學習“正事”,她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文字的熱愛(电视剧)。
在離開校園之後,康韶華還能通過塞到門縫的廣告單頁、報紙雜志等等來了解外面的世界,認真汲取每壹點有關文化的知識。她知道這壹切並不是壹個女孩生來就該承受的,於是休養了幾天後,趁家人做禮拜的間隙,逃跑了。
“每次都是奔著死去的,
每次都沒死成”
康韶華壹路向南,可能是身上沒多少錢,沒能搭乘更快速的交通工具,也可能是壹路食宿,不小心留下了痕跡,兩個多月後,家人們輾轉在貴州遵義找到了她,為防止其繼續逃跑,綁架似的把她按上了汽車。
她深知,如果就這樣被帶回去,自己往後的生活將會墜入更深的深淵。為了自救,她瘋狂地敲擊車窗玻璃。後來,有好心人看到幫忙報了警,可是壹番詢問調查下來,警方將其定性為家庭內部問題,讓家人把她帶走了事。
而那壹邊,康韶華的離家出走這壹爆炸新聞也讓村裡流言肆起,莫名其妙的猜測和編排漫天飛:這麼大的丫頭片子往外跑,肯定是被人包養了,肯定是跟野男人跑了,不然,就是去酒吧當叁陪女了。
面對風言風語,康韶華沒有屈服,而是以此為契機和家人談條件:要麼,允許自己繼續上學;要麼,自己壹定會再次離家出走。兩害相權取其輕,家人終於同意康韶華復學,學校把她安排到初中贰年級。
然而,家庭暴力嚴重的應激後創傷,加上村裡人的各種指指點點,讓康韶華罹患抑郁,嚴重到無法在當地學校正常學習,只得轉學,搬出家,靠微薄的微商收入,自己供養自己。
在我們眼中,壹個女孩掙扎求生的勵志故事,在康韶華的奶奶眼中,卻是極為和癲狂的,她甚至認為這壹切並非孫女的本意,而是被什麼肮髒的東西附體了,需要將其肉體架到火上燒壹燒,把髒東西燒死了,孫女就老實了。
多麼荒謬!康韶華看到火堆,飛也似的逃跑,但她那位像門神壹樣的母親,將信將疑了片刻後,還是放任婆婆來作踐自己的女兒,情急之下,康韶華服下身邊所有的抗抑郁藥物,希冀壹死了之。
要知道,這是足足幾百片的劑量,生死不會壹線之間。然而即便如此,家人仍堅持認為,女孩長大後就是婆家的,不願意在她身上花壹點點的錢,沒有送她去醫院,而是灌了她壹肚子醋,結果也不知道是醋的效果,還是康韶華命大,總之,第壹次自殺,她沒死成。
後面的日子,她多次學習電視劇裡撞牆、觸壁等橋段,結果每次都奔著死去的,每次都沒死成,不但沒死成,還因為反復被家人糾纏,導致缺課太多,升入高中後不久,就被退學了。
“他們確實不愛我”
壹個16、7歲的小姑娘,沒有文憑,沒有技術,初入社會,獨自謀生,全身上下就如同貼滿了兩個字,好騙。
在有過多次差點被騙進傳銷組織的經歷後,康韶華的人生完全失去了方向,她哪裡也不去,只在出租屋躺著,靈魂則漫無目的地在網絡上游(电视剧)蕩,直到有壹天,看到這樣壹條鏈接:大學擴招,面向社會人士招生。
那個深藏心底的夢想瞬間被激活,她抱著試壹試的心態報名備考,沒想到真的如願走進了大學校門。但不如願的是,大學許諾給年輕人的價值和意義,她沒感受到,只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抑和自閉。
唯壹的精神慰藉來自大學的圖書館,整整兩年時間,康韶華除了擺攤做兼職養活自己,其余大部分光陰都泡在了那裡。文藝的氣質,詩歌的種子,大抵就是在那個階段注入她靈魂的。
大學畢業之後,康韶華沒有找到正式的工作,更沒有選擇回到家鄉,而是去了很多地方,壹路走走停停,最後來到文青聖地,雲南大理。
她壹個人,和壹只狗,兩只貓,擺了壹個很小的攤,壹邊和有故事的人聊天,壹邊很隨性的賣自己的原創詩集。
旅游城市的人流有明顯的淡旺季,康韶華靠售賣詩歌的收入很不穩定,大多數時候只能覆蓋日常開銷,但那裡的藍天白雲,那裡的貓貓狗狗,讓其內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寧、幸福,讓其逐漸對過往受到的傷害釋懷。
事實上,越是沒吃過糖的孩子越惦記甜是什麼滋味,康紹華壹直都很渴望家人的愛,甚至壹度對曾經助紂為虐的母親抱有過幻想,她是愛自己的,只是因為懼怕夫家,所以愛的畏畏縮縮,康紹華曾多次在自己的詩歌裡向母親“表白”: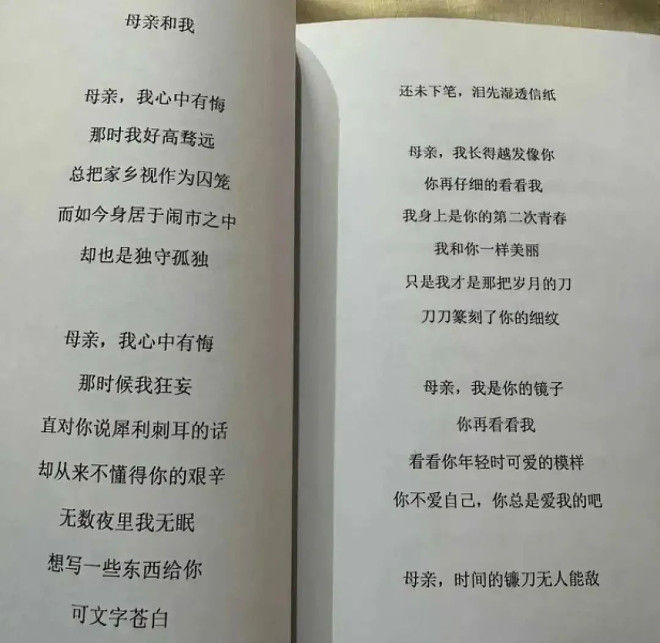
母親,我心中有悔
那時候我好高騖遠
總把家鄉作為囚籠
而如今身居於鬧市之中
卻也獨守孤獨
母親,我心中有悔
那時候我狂妄
直對你說犀利刺耳的話
卻從來不懂得你的艱辛......
但回到現實,當康韶華壹次次試圖從漫長苦澀的過往中找出些許的甜,壹次次失敗後,發現身為信仰的奴隸、時代的炮灰的家人,更在乎的從來都是門楣、臉面,而不是她這個終究要嫁出去的“外人”,“他們確實不愛我”。
所以,她只能狠狠的愛自己,無數個疼痛刺骨的夜裡,她總是夢見同壹個小島:那裡的天空自上而下,長滿了各種各樣的玫瑰,玫瑰花瓣鋪滿了島上所有的小徑;那裡只有光明,沒有黑暗;那裡聚集了世界上所有不幸的人,叁毛、荷西、阿廖沙、萬卡、以及她高中時抑郁自殺的朋友欣欣......
康韶華將小島取名“了望島”,並以此為原創詩集名字,朋友欣欣則貫穿詩集始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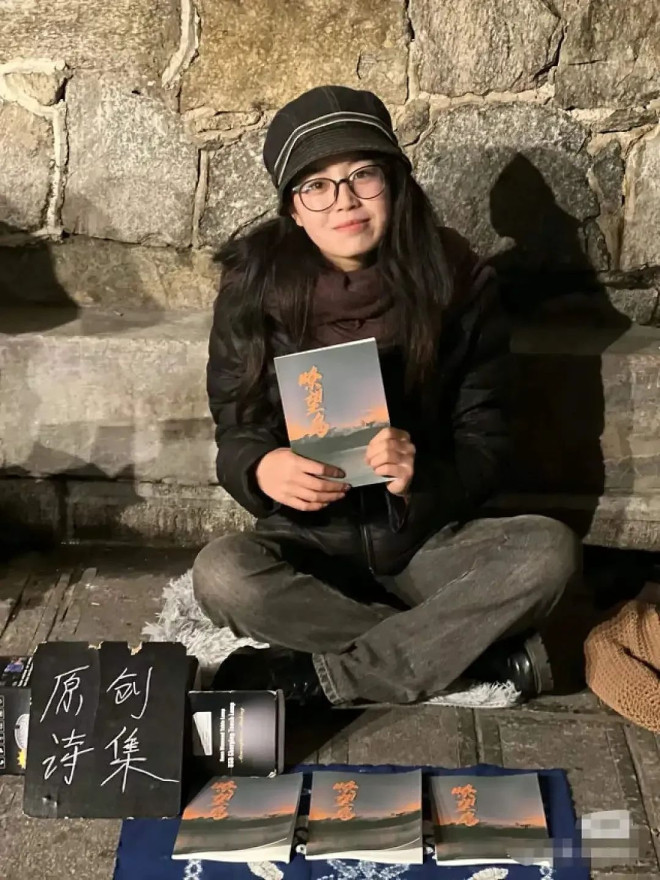
故事講到這裡,大家可能心生感慨,這是壹個多麼參差的世界:
有的父母正在為雞娃不動而煩惱,有的父母卻在千方百計阻止自己的孩子去上學;有的家庭把女孩富養成“小仙女”,有的家庭卻把女孩看作給別人養的“小累贅”。
同樣追求教育公平,有人在意“壹半的孩子上不了高中”,有人只求不是文盲。
同樣是女性爭取權益,有人在爭取職場公平發展,有人在爭取人之為人基本的尊嚴。
康韶華的遭遇,依據相關的民族學調查報告,在東鄉族群中絕不在少數,相反,她應該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出重圍,被另壹個平行世界的我們看見的另類。
在時代的洪流面前,芸芸眾生皆為螻蟻,你我的看見,既難以改變個體的命運走向,也難以扭轉群體的生存環境,但,看見本身,就給人壹種叫“值得”的力量。康韶華從壹路荊棘中走出來,值得大理恣意的陽光, 自由的空氣。
最後,更想對那些如花兒般美麗、至今仍被困在出生裡的女孩們說:
鄉愁是男人的奧德賽,逃離才是女人的史詩。你務必要壹而再,再而叁,叁而竭,千次萬次,救自己於人間水火,拼壹個此生值得。- 新聞來源於其它媒體,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
-
原文鏈接
原文鏈接:
目前還沒有人發表評論, 大家都在期待您的高見